我在整理一箱要捐给慈善商店的书时发现了这张照片。它被夹在一本精装的数据书里,这种书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了。一张8英寸乘10英寸的光滑印刷品,由该部门过去雇用的专业摄影师精心制作。在这张单色图片中,三排穿着可疑的原始实验室大褂的人或坐或站,摆出正式的姿势。我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更仔细地看了看这幅画。岁月飞逝,我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潜伏在第二排,站在海伦旁边,而海伦旁边站的是戴夫而不是我。当时我们二十五六岁,深信自己无所不知,准备改变世界。
有一段时间,我想我们确实改变了一些事情——尽管它演变成了一个有趣的死胡同。看了看照片的背面,我发现它的日期和我们第一次结婚的年份一样自然纸,所以这可能是为了宣传的媒体形象。当我想起我们当地报纸上的标题——“实验室科学家追踪时间裂缝”时,我暗自笑了笑,这种说法表明我们对我们真正的成就一无所知。看着一排排的人,我开始把名字和脸联系起来,这是我记忆的一个壮举,除了一个:一个成熟的女人,深色头发刚开始变白,可能快40岁了。我扫描了指纹,并在墙上的屏幕上放大了图像,这给了足够的分辨率,使她的VRW徽章。所以,一个访问研究工作者——但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把扫描图寄给了海伦和戴夫,他们现在还在一起,我想提醒他们我们曾经有多年轻,并问他们是否认识我们的神秘同事。事后想起来,我提议一起吃午饭——他们都同意了,就在火车站旁边的那个新地方安顿下来。课间,我拿出照片,问他们是否有什么想法。戴夫把剩下的头发往后梳,摇了摇头。“我有点认识她的脸,但记不起她的名字。对不起……”海伦摆出一副冷淡而中性的表情。“一个科学界的隐形女人。真不寻常……”
“那是茱莉亚,”她接着说。“我想是茱莉亚·费尔南德斯。她只在实验室待了一个月左右。她的英语不太流利,也不太会说话,但她教了我一些很棒的西班牙语脏话……”海伦又看了看那张纸。“不过,她在理论方面有一些很好的想法,而且她的很多调整都进入了生产环节。事实上,回想起来,我怀疑她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戴夫慢慢地点点头。“是的,既然你提到了,我记得她和斯派克之间有点麻烦。他真的不喜欢被告知他的传感器阵列代码是垃圾——尽管她的mod使例程效率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实际上,我在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否会看到这种效果——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粒度。我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阅读Nature Futures的更多科幻小说
但是主菜上来了,这一刻就没了。过了很久,在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下午,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之后,我迅速地找了她一下。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在搜索“朱莉娅·费尔南德斯”时,出现了大量可能的匹配——所以我放弃了,转而在实验室照片上进行了图像搜索。唯一被点名的是该实验室当年的年度报告——但只有主任和高级管理团队被点名。
在煮咖啡的时候,我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把茱莉亚的头和肩膀从图片上剪掉,把她放在一个普通的背景上。再次运行图像搜索,我得到了进一步的匹配结果,但这个匹配结果让我无法找到其他的东西,而不是咖啡。
戴夫和海伦似乎都对这么快又见面的邀请感到困惑——但他们还是来了,我把啤酒和点心放在他们面前。
“嗯?你不再神秘了吗?海伦问道,赞许地尝了尝她的印度淡啤酒。
我点了点头。“是的,我想我可能找到她了——茱莉亚。”我把平板电脑滑过桌子,他们看着这两张图片,然后交换了眼神。
“嗯,肯定是同一个人——看看眼睛就知道了。”戴夫说。“但是……在另一张照片里,她一定要年轻20岁——或者更多。你在哪儿找到的?”
我伸手在屏幕上滑动,弹出了一个公司联系页面。“各位,来认识一下朱莉娅·费尔南德斯,她目前是新墨西哥州准自然事件研究所的研究生。22岁。她的传记把她的专长列为‘时间异常’……”
在随后的沉默中,海伦喝了一大口啤酒。“这么说,”她平静地说,“这就是近40年前到我们实验室来的那位女士?那时她大概比现在大20岁吧?在那次访问中,她推动我们的项目寻找‘时间风暴’——或者小报怎么称呼它们——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点点头,不敢开口。也许我们的研究并不是死胡同。
戴夫紧张地笑了。“也许我们应该给小茱莉亚寄一份我们的原始论文?”这可能正是她所需要的,让她走上正确的道路,去发现她会发现的任何东西。”
海伦皱起了眉头。“等一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呢?如果小茱莉亚从来没看过报纸怎么办?她还能联系我们吗?我们的时间线改变了,论文就写不出来了吗?”
我在回答之前喝了一杯。“恐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你是说……?”
“是的,我今天早上寄给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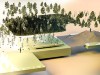 John Gilbey的《分水岭》
John Gilbey的《分水岭》 John Gilbey的早期预警
John Gilbey的早期预警 约翰·吉尔贝的《至日》
约翰·吉尔贝的《至日》 John Gilbey的《突破》
John Gilbey的《突破》 John Gilbey的《Geode》
John Gilbey的《Geode》 约翰·吉尔贝的《城堡》
约翰·吉尔贝的《城堡》 约翰·吉尔贝违规
约翰·吉尔贝违规 约翰·吉尔贝的深刻印象
约翰·吉尔贝的深刻印象 《2062年回顾》作者:John Gilbey
《2062年回顾》作者:John Gilbey 通讯员John Gilbey
通讯员John Gilbey 约翰·吉尔贝《拜访鲍勃》
约翰·吉尔贝《拜访鲍勃》 John Gilbey和Brian Malow的干预
John Gilbey和Brian Malow的干预 John Gilbey的最后一个实验室
John Gilbey的最后一个实验室 约翰·吉尔贝在消磨时间
约翰·吉尔贝在消磨时间 John Gilbey的纠正措施
John Gilbey的纠正措施 约翰·吉尔贝未完成的事业
约翰·吉尔贝未完成的事业 由John Gilbey撰写的最终协议
由John Gilbey撰写的最终协议 John Gilbey的承诺
John Gilbey的承诺 永久职位:约翰·吉尔贝
永久职位:约翰·吉尔贝 John Gilbey与Max的会面
John Gilbey与Max的会面 约翰·吉尔贝报道
约翰·吉尔贝报道 约翰·吉尔贝为大戴夫做的最后一搏
约翰·吉尔贝为大戴夫做的最后一搏 John Gilbey的《寻找中庸》
John Gilbey的《寻找中庸》 John Gilbey在VR中从不下雨
John Gilbey在VR中从不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