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图源:吉纳·穆恩/彭博,盖蒂图片社
在过去二十年中,致命国际疾病爆发的间隔时间缩短了,而这些疾病爆发的人力和经济代价却增加了。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导致800人死亡,经济损失400亿美元。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造成1.1万多人死亡,经济和社会损失530亿美元。2020年初,COVID-19在全球迅速传播,估计已造成1700多万人死亡,到2024年经济损失估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拖延向世界通报这些威胁导致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多的生命损失。
下一个传染病威胁可能更加致命,代价也更加高昂。政治领导人可以选择阻止它。2021年5月,我们和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的同事们发布了一套基于证据的转型变革行动,可能使COVID-19成为最后一次具有这种破坏性的大流行(见go.nature.com/3iqfqhm).简而言之,我们建议改变观念,由独立的、资金充足的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更快地发现和报告疫情和威胁。各国总统和总理将领导一个委员会,协调多部门行动并促进问责制。医疗对策将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提供。这个改革后的系统将得到一个国际基金的支持,该基金为预防和应对新的健康威胁的措施提供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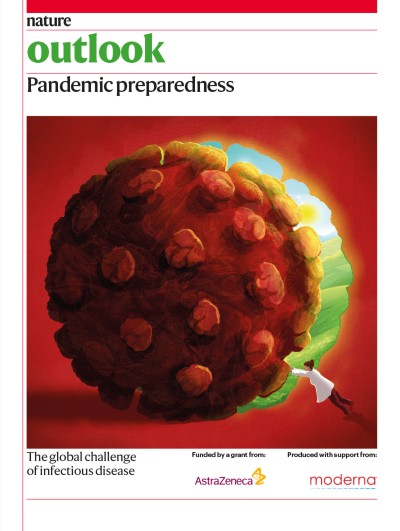
《自然展望:大流行防备》的一部分
为了阻止下一个卫生威胁,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必须在全国和团结一致地发挥带头作用。尽管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卫生、经济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但除了一些例外,它的特点是说得太多,做得不够。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峰会宣布了令人欢迎的资金支持,各国领导人也在世卫组织会议上发言,但行动并未持续下去。
我们认为,需要一个领导人级别的全球理事会,以确定防范和应对方面的差距,调动资金,追究公共和私营利益攸关方的责任,并在出现威胁迹象时发挥领导作用。该理事会应由联合国大会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政治宣言来设立。
据估计,全球大流行预防每年耗资105亿美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与没有做好准备的成本相比只是零头。今年6月,世界银行董事会批准了一项用于大流行预防、准备和应对的新基金,但它太新了,无法进行适当的评估。然而,早期迹象表明,该基金基于过时的“捐赠-受益”模式,高收入国家的影响力过大,而认捐的资金不足。相反,我们建议采用包容性的全球公共投资融资模式,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一席之地,并根据国家的需求和财政状况支付资金。
还必须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如果要继续发挥全球卫生协调机构的作用,会员国必须赋予它权力、独立性和资金,使其能够很好地发挥这一作用。当SARS-CoV-2病毒出现时,世卫组织迟迟没有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目前正在努力修订指导全球应对国际公共卫生威胁的《国际卫生条例》,以明确授权世卫组织就疾病爆发自由沟通,根据证据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受阻碍地进行调查。然而,这些修正案要到2024年5月才会被接受,而且要到更晚的时候才会生效。这造成了一个危险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世卫组织必须大胆行动,并在出现新的威胁时发出警报。它对当前猴痘疫情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对速度是令人鼓舞的,尽管一些人认为它应该更早到来。

更多信息来自《自然展望》
改革面临来自工业界和一些国家的最大阻力的领域是保证在最需要的地方提供适当的医疗对策。疫苗和疗法是全球共同利益——它们的目的是在突发卫生事件期间减缓疾病传播和保护生命,而不是牟利机会。应对措施应根据公共卫生需求公平分配,研究和开发必须针对这些产品需要运行的环境进行调整——例如,“超冷链”疫苗不容易在温暖的低收入国家提供。
对2020年4月启动的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的成败进行评估,应能揭示实现公平制度的切实可行的下一步步骤。世卫组织目前正在谈判的大流行防范条约还将确保建立从研究和开发到交付的端到端医疗对策系统,该系统考虑到所有收入水平国家的公共卫生需求。这些考虑必须包括支持全球制造业,以防止富裕国家在突发卫生事件期间以牺牲低收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优先考虑本国人口。
这些建议并非详尽无遗。其他行动,如建立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信任,以及投资于将病原体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风险降至最低的战略,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领导人现在有一个明确的选择:观察一种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疾病的出现和传播,或者为阻止它奠定必要的基础。考虑到COVID-19造成的破坏,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选择。

 让世界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让世界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在大流行期间掌握说服的艺术
在大流行期间掌握说服的艺术 使卫生保健系统为未来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使卫生保健系统为未来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寻找可能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
寻找可能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 算法能预测下一次大流行吗?
算法能预测下一次大流行吗? 为什么气候变化对大流行防范至关重要
为什么气候变化对大流行防范至关重要 用远紫外线消毒空气
用远紫外线消毒空气 如何根除下一次大流行疾病
如何根除下一次大流行疾病 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的五种方法
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的五种方法





